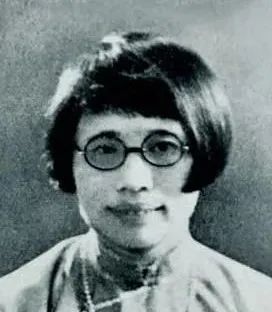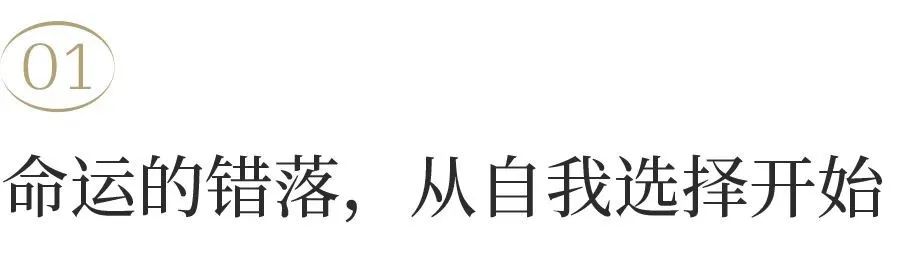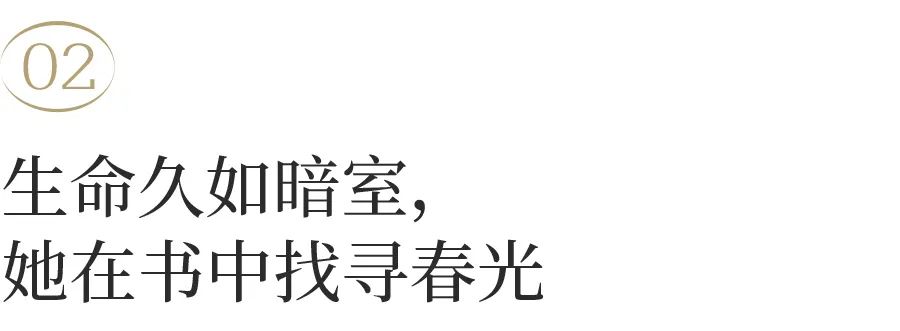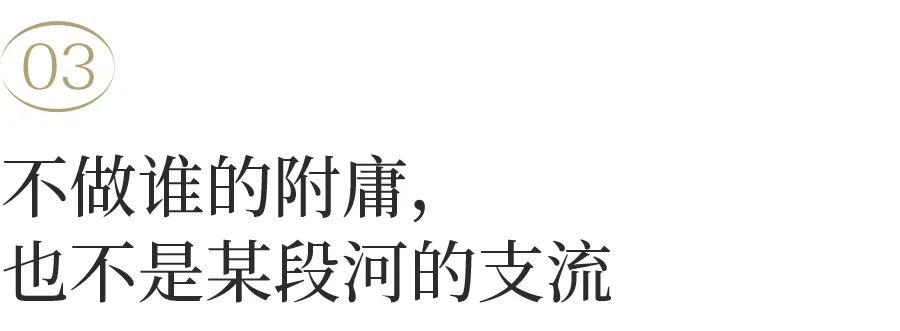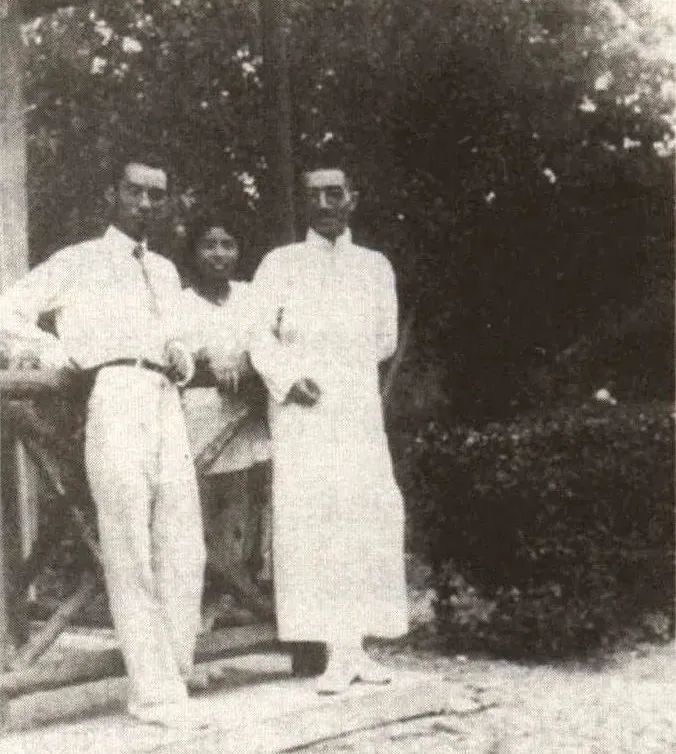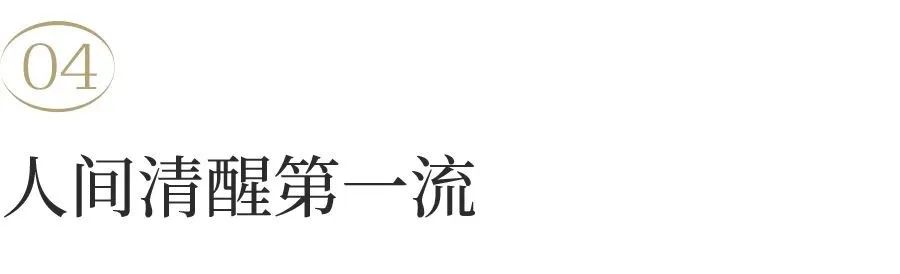|
她是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教授,培养出了林徽因、张爱玲、谢婉莹等一众才女,被称为“才女之师”,但很多人却并不熟悉她的名字。 她还是中国第一位白话文女作家,民国女性主义先锋人物。从立志独身到结婚生子,她对于爱情和婚姻始终保持高度清醒。 晚年的她经历了不公平的待遇却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她曾说:“中国人喜欢一时冲动,但不会一直头脑发热。” 她就是一生堪称“造命”的传奇女子——陈衡哲。
陈衡哲/ 网络
1890 年,陈衡哲出生在江苏武进的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曾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父亲是晚清时期的举人,颇有学识,母亲出身于江苏名门望族,擅长作画与书法。陈衡哲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四岁就开始读《黄帝内经》和《尔雅》。 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女子脚小才漂亮,天足会被人耻笑,对于陈家这样的传统书香名门更是如此。八岁的陈衡哲也被母亲强制着缠上了长长的裹脚布,但骨子里不服输的陈衡哲可不想一辈子被困在斗室之中。她趁着母亲转身走开,立马解开裹脚布。 就这样裹了拆,拆了裹,折腾了数个回合,女儿反抗的力量超过了母亲要为其裹脚的决心,遂就此作罢。彼时,年幼的陈衡哲还不知道,正是这双“天足”让她在未来得以拥有行走四方、求学海外的自由。而命运的转变与错落,皆从自我选择开始。 陈衡哲十三岁那年,她的父亲要去四川做官,母亲随行,舅舅便建议陈衡哲跟随自己去广州上学。 当时,广州招收女生的学校只有一所女子医学院,可当陈衡哲去报名的时候,才发现学校只收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无奈之下她只好先住在舅舅家,由舅舅教授她国文。但陈衡哲向往学校,不愿意天天待在家里读书。于是舅舅将她送至上海,委托朋友代为照顾,并推荐她进入上海爱国女校学习,当时这所女校的校长正是蔡元培。但不凑巧的是,学校此时已经放假,陈衡哲只好在表哥的安排下就读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学习中医、西医和英语。虽然陈衡哲不喜欢学医,但她在这所学校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为之后的赴美留学创造了机会。
毕业这一年,接到父亲的信后从上海赶回四川的陈衡哲,发现父亲竟为她物色了一门亲事。在父亲的眼中,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要讲究门当户对,唯有出身官宦世家的富贵公子才算是女儿的好姻缘。 但是陈衡哲对这种包办婚姻持极力反对的态度。她觉得女人不应该被困在宅院一隅做贤妻良母,更要活出自己的价值,而摆脱宿命的唯一方法就是读书。就这样,这门亲事在陈衡哲的抵抗中“夭折”了。为了逃避父母的“催婚”,陈衡哲干脆躲到了乡下的姑母家。 这位姑母对于陈衡哲有着非凡的意义,她如同召唤黎明的一抹霞光,让陈衡哲更坚定了未来的道路。
陈衡哲/ 网络 只可惜好景不长,在姑母家住了三年后,陈衡哲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姑母虽然懂中医,会书法,并能以此营生,但不承想她的儿媳妇和儿子竟双双染上了大烟,导致家庭收益入不敷出,生活陷入泥淖。此时,陈衡哲的父亲也失去了工作,母亲开始教画画支持家庭开支。陈衡哲只好在姑母的介绍下,到一户富人家当起了家庭教师。 这般晦暗的日子对陈衡哲来说简直度日如年,但决心“造命”的她怎会一直沉沦。即使命运将她困于暗室,她也要挣扎着在书中找寻春光。某天,陈衡哲在报纸上看到清华学校的招生考试信息,合格者能获得公费赴美留学的机会。陈衡哲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却有些犹豫,毕竟考试科目中有一半是自己从未学过的。姑母知晓后,却让她无论如何都要试一下。 就这样,在姑母的鼓励下,陈衡哲参加了这次考试。好在命运永远不会苛待努力奋进者,陈衡哲成为第一批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
来到美国后,陈衡哲也没有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她一边认真完成学业,一边坚持给留美华人创办的期刊投稿,并以一篇《莱因女士传》受到《留美学生季报》主编任鸿隽的青睐。随后,她以“莎菲”为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了一年。而这篇小说的发表也为她带来了一批追随者,其中就包括大才子胡适。 任鸿隽与胡适是至交好友,比陈衡哲大了四岁,虽一直倾慕陈衡哲,却将这份感情藏得很深。直到胡适和陈衡哲无奈分开,他才有了吐露心迹的机会。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的合影 / 网络 1919年,学成归国的任鸿隽受政府委托,前往美国考察炼钢技术。第一站,他就选择了陈衡哲所在的芝加哥。在此期间,任鸿隽不断向陈衡哲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任鸿隽在与陈衡哲相处的过程中,始终给予对方宽裕的个人空间,支持陈衡哲的独立思想。他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个天才女子。” 有些人因相爱而相知,有些人因相知而相爱,无论哪一种都是令人歆羡的。任鸿隽的爱是不必说出口的懂得,更是沉默无言的成全,他明白她不愿做谁的附庸,更不是哪条河的支流,她就是她,是独一无二、决不妥协的陈衡哲。
1920年,北京大学正式开始招收女生,开创了中国男女同校的先河。同年,陈衡哲跟丈夫任鸿隽一起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主教戏剧与西方历史课程。 陈衡哲更是凭借中国第一个女教授、第一个女硕士的光辉履历,为北京大学招收女学生营造氛围,开辟新风。无论在中国教育史,还是中国妇女史,陈衡哲的存在都像是一个宝贵的历史印记,标志着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 在北大任教期间,陈衡哲教出了许多日后在各行各业闪闪发光的女性学生,包括林徽因、张爱玲、萧红等。因此,她也被后人称为“才女之师”。
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 / 网络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无数人被迫中断学业。在国破家亡的困境中,陈衡哲夫妇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辗转各地。 在任鸿隽的呵护下,陈衡哲的成就更加卓越,她受邀到西南联大举办讲座,盛名引来了大批听众,教室座无虚席,清华、北大的教授都要站在角落静听。就连周恩来在接见她的时候都说:“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 战火纷飞的年代,虽难寻安稳,陈衡哲却从未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她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她的悉心培养下,长女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二女儿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最小的儿子也获地理学博士学位。 有人说,陈衡哲最终选择结婚生子是对不婚主义的背叛,是对社会现实的妥协。其实不然,她一直是理智至上的清醒者,从未改变分毫。 为倡导女性解放,她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她主张男女平等,女性应自主自立,但不能因此敌视男人,因为不满就从家庭中叛逃的过激行为更是不可取的。她提倡的妇女解放,是让妇女的社会价值得到重视,但不意味着女性必须丢掉家庭价值。她认为妇女解放不是为了所谓的个人价值,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而是要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与男人平等相处,给丈夫、子女、家庭,乃至社会带来良好影响,达成多赢,这才是最终目的。她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明白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1976年1月,陈衡哲因肺炎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她的一生可以以这句话作注解:“人的一生只有一件事不能选择,就是自己的出生,其他一切命运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以上内容摘自《如花在野 温柔热烈》,部分内容有删改,作者是赵健。
《如花在野 温柔热烈》 赵健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近代百年,波翻浪涌,女性从未缺席。林徽因、杨绛、杨苡、潘玉良……她们左手科学,右手人文,追赶日月,不苟于山川。 《如花在野 温柔热烈》记录了23位民国女性的成长故事,揭示了那些光鲜称谓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她们犹如悬崖上迎风绽放的花朵,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坚韧的精神闪耀在历史舞台上。 原标题:《她的存在,标志着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