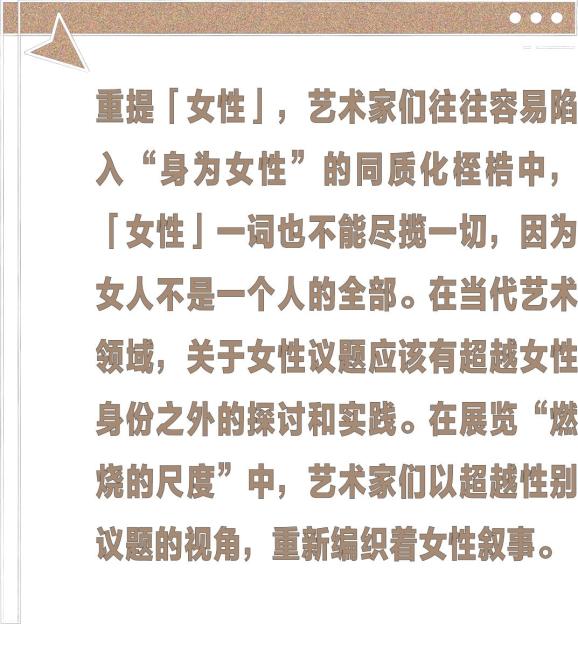|
在谈及不同的种族与阶级时,面临的生活境遇截然不同的“女性”是否具有统一身份特质这一问题时,美国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曾说:“如果一个人‘是’女人,这当然不是这个人的全部;这个词不能尽揽一切,不是因为有一个尚未性别化的‘人’,超越他/她的性别的各种具体属性,而是因为在不同历史语境里,性别的建构并不都是前后一贯或一致的,它与话语在种族、阶级、族群、性和地域等范畴所建构的身份形态交相作用。”身为女性是否可以天然地获得关于女性主义的主体身份及其意识?关于女性议题的讨论是否拥有“身为女性”(性别化)之外的方式?
“燃烧的尺度”展览现场,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2024年。 图片由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提供 正在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进行的女性艺术家群展“燃烧的尺度”,或许正是我们从眼下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现实——基于女性性别身份的公共讨论以及女性群体抗争实践中短暂抽离,将目光聚焦在以女性艺术家的实践本身,甚至是在一种超越性别议题的视野中重新编织女性艺术家的新叙事。 对于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沈奇岚来说,女性艺术家出现在一个展览中不意味着其自动(及需要)获得与女性主义话题的联结。公共领域对于女性主义的讨论与女性艺术家主体的艺术实践之间,并不存在先天的联盟。尤其在对女性主义的讨论已经成为社会观念变迁的普遍现实的当下,早期女性艺术家(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通过艺术实践传递女性主义诉求的工作方式,或许已经让位于作为人类个体在垂危现实中如何寻求自处这样更为紧迫的问题。 在当代艺术领域,将女性主义作为方法或内容,是艺术家可以采取的诸多策略之一。即使是在以女性主义为前提的艺术实践中,女性艺术家的实践实际上针对的是对过去女性(如果我们可以将“女性”视为一个稳定的整体)历史中的缺失,以及社会现实中依然未能得到解决的女性主义问题——例如,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 GGGI)报告指出人类距离性别平权尚需132年——作出回应。需要注意的是,女性主义议题在这里已经逐渐成为多元文化与意识形态现实的一部分,在这种全新的语境中,女性艺术家需要对(曾被以为)附加在女性艺术家主体上的性别属性实施超越。
上&下:“燃烧的尺度”展览现场,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2024年。 图片由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提供 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女性艺术家实践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大于不同性别艺术家实践之间的差异。那么本体论式的——例如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讨论在艺术实践中即使不是毫无价值,也不应该成为女性主义话题的唯一焦点。在继续讨论女性范畴能否被建构为统一、稳定的整体的同时,是不是也需要反过来对前者暗藏的与女性主义诉求背道而驰的“对性别关系的一种不明智的管控和物化”(Judith Butler语)提高警惕?
“燃烧的尺度”展览现场,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2024年。 图片由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提供 从这个角度看,“燃烧的尺度”正是对于眼下女性主义以及被冠之以女性主义艺术实践中弥漫的同质性现象的回应。沈奇岚提到:“当众人将聚光灯集中在性别议题上的时候,舞台上的其它角落就无形中被遮蔽了。当然,性别问题需要以某种方式被聚焦,但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去观看舞台上没有被照亮的角落。”并以此挖掘、发现并呈现女性艺术家群体有可能被忽视的创作(燃烧)强度。
左:尹秀珍,《融器-红色斧子》,2015年,陶瓷,斧头。 右:《融器一尺No.3》,2017年,陶瓷,尺。 图片由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提供 例如艺术家尹秀珍的作品《融器-红色斧子》,自2016年展出后就再也没有公开展览过,而这件作品中包含的潜能在展览所处的全新语境中被重新激活。对沈奇岚来说,艺术家在此不仅仅创造了一件作品,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对暴力的解决之道:在燃烧的过程之中,象征暴力的利斧已经内嵌、共融于其原本试图去摧毁的对象中。尹秀珍试图用作品去“缝合”过去曾被认为是难以弥合的裂隙,在这件作品中,陶瓷和金属(铁)在炉火淬炼的过程中不断较量、渗透与融合,是“撕裂和缝合过程的凝聚物,也是这些不同物质相互作用后产生的能量承载物”。
付小桐,《68,508孔、77,176孔、130,095孔、56,220孔》,2023年。 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而在艺术家付小桐的作品《68,508孔-77,176孔-130,095孔-56,220孔》(2023)中,被绵密的劳作和决心反复穿透的宣纸上显现出的山水图像,无疑让人想起被男性主导的中国传统书画史,以及女性的劳作与创造被长期限制在私密空间中的历史。“刺”意味着“穿越”和“破坏”,在如此艰辛的日常劳作中,必须拥有“愚公移山”般的坚韧,“就好比心中有一片茫茫无际沙漠,你要一粒一粒沙子数过去,明知无望,但求心之所念。在制作过程中,针刺的力度和节奏是均匀和平静的,不带任何情感,我希望放下任何杂念。”但与此同时,付小桐的作品最终仍然是合于中国传统宇宙观中的山水意识的。只不过在艺术家的作品中,中国山水画强调的“天人合一”以一种具身化的方式,并在“触觉视觉”的画面质感中得到彰显。
“燃烧的尺度”展览现场,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2024年。 图片由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提供 尹秀珍:女性议题成为重要的关注点是与女性自身的觉醒和作为密不可分的。性别本身本不应该成为孰重孰轻的话题,但漫长的对女性价值忽视的历史迫使女性强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强调自身价值重要性的同时,争取本应平等的权利。不同代际的女性艺术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有所不同,我特别敬佩那些最初为女性发声的艺术家,那是要冲破固化的歧视女性的社会环境所作出的具有强大勇气的举动,很是值得尊重。现如今的世界,女性艺术家已经成为艺术的焦点之一,女性特有的看世界的方式也被不同的艺术家不断地用艺术作品传递出来。现在很多女性艺术家不以“性别”作为标签和元素进行创作了,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平等的人,用作品呈现自己的认识更加重要。
“燃烧的尺度”展览现场,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2024年。 图片由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提供 付小桐:说到女性艺术家,自然会有强烈的历史带入感,女性本身在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是一个“失语”状态,女性艺术创作过程就是缓慢地自我觉醒的过程,中国女性艺术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着明显的变化,走出闺阁,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个体身份,并不断向束缚自己的传统观念挑战,直到今天女性可以通过艺术创作探讨个体与权力、欲望与身份等议题,当然受益于时代的变化以及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从民国到新中国,以及到当下,艺术创作有着巨大的变化和差异性。观看几代人的作品,你会清晰地看到女性是如何从社会对其身体和思想的规训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整个过程。女性艺术家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与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不同的历史时期看有着明显的时代共性,因为大家面临着相同的社会问题。例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是一个历史巨变中充满生机的时代,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来投身社会,跟随社会变革,开始迅速觉悟。艺术创作风格也从过去的阴柔、抒情中走向表达恢弘的气势。 在20世纪末,尤其在经历了“85美术新潮”的冲击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艺术家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向世俗挑战。例如“塞壬工作室”中的艺术家李虹、袁耀敏、奉家丽、崔岫闻,以及喻红、刘丽萍、蔡锦、申玲、林天苗、尹秀珍、施慧等等上一代艺术家的实践,都在时代变革中勇敢地抗争、质询、排斥和找寻自我,在种种的精神矛盾和冲突中辨识和确认作为女性的主体。直到最近一段时期,艺术界对女性议题的关注,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实际上是数代女性艺术家群体不断实践才最终取得的局面。 尽管我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并不想刻意去强调女性身份,但这是一个历史烙印和性别属性,没有办法避开,只要你进行艺术创作,就不得不面对生命本身。
“燃烧的尺度”展览现场,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2024年。 图片由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提供 尹秀珍:当不断地强调“性别属性”,是对女性不够尊重的体现。人是平等的,性别议题本身就是“不平等”造成的。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都会有优秀女性和优秀男性的涌现,社会应给与平等的对待和关注。当全社会不再以性别作为议题的时候,女性才真正地获得了平等的地位。 美国哲学家Donna Haraway曾说:“没有任何事是天生就与‘女性’联结在一起的,甚至没有一个称作是‘存在’的(being)女性”。特别是在今天,女性主体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处在流动中的不稳定的主体,这种不稳定非但没有削弱女性主体地位,反而让女性对于其主体身份拥有更加多维的自我定义及日常实践的可能。Donna Haraway提出了以“赛博格”(Cyborg)这样“一个关于政治身份的神话”将女性主体塑造成超越目前的各种身份认同困境(比如种族、阶级、性别等),创造一个全新的、平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人类生活方式。“宁做赛博格,不做女神”,Haraway试图“保持不相容的事物在一起的紧张状态”,并以“一种共生的乌托邦或后恋母情结启示来治愈严重的性别裂缝”。 正像我们在艺术家田翊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性别议题已经被更加切身、具体的问题(例如不同生命与非生命存在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取代。对她来说,看待不同代际的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和看待一般艺术史的角度没有任何差异,无非是社会背景、材料技术和心理健康等等层面。
田翊,《无法舍弃的蛹》,2023年,陶瓷。 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田翊:我自己在创作中或者生活中,并不经常从性别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或者决定喜好。所以,对于艺术家及其创作(或者别的职业),以性别来做专业讨论这件事,我很难代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过去的历史进程及先天的生理因素已经将性别在社会分工中的角色刻画得很深了,事实确实是女性在许多专业领域的人数比例都落后于男性。因此在我看来,讨论女性或者女性艺术家可能应该是对过去缺失的一种补充。 在创作的时候我没有去刻意结合自己的性别经验,“某种共性”或者“女性议题”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但是我无法决定别人以什么方式阅读作品,或者想从什么角度理解它。
上&下:“燃烧的尺度”展览现场,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2024年。 图片由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提供 基于对“基因折射”这一观点的兴趣,田翊近期的创作大多与自然科学及生物学有关。“不同于线性的逻辑思维,生物信息或遗传密码中的因果关系通常是不太直接的。随着科技发展带动了观测方式的层层推进,尽管可读取的信息变多了,但可能观测者并不觉得自己对这些生物有了更多的掌握或把控。相反,这些发现可能按顺序出现,但他们之间并不相关。就像你从包装中取出的下一块拼图不仅无法咬合第一块(接头不合适),而且其表面的图像也不连贯。然而,也许你可以从这两块拼图在图像上共享的相似元素中,猜测它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和位置关系。”艺术家被这种碎片形式的信息传递方式所吸引,并在与生物学研究者进行合作后,获得了若干生物生理构造的形态,并“以有机的姿态,与人造物或者风俗景观,相互融合、拟态或者占领”。
不以生理性别去评判艺术家的创作,而以其创作意识——例如同情心、同理心,一种在彰显自身的同时亦能够试图理解他者的状态,去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判定。
在“燃烧的尺度”中,女性主义是理解展览的一个维度,但绝非唯一维度;同时,在沈奇岚看来,这种女性主义的维度指向的是一种对于“真正的女性意识”的探究。“不以生理性别去评判艺术家的创作,而以其创作意识——例如同情心、同理心,一种在彰显自身的同时亦能够试图理解他者的状态,去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判定”,“燃烧的尺度”探讨的是一种强度,一种直面女性艺术家创作本身而产生的更加深刻和广泛的强度。
刘昕,《环骸》,2021年。 图片由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提供 从尹秀珍到刘昕,能量在消耗的表象中获得了熵增的矛盾统一,无限向下与无限向上的力成为宇宙能量新陈代谢的一种基本模式;从陈萧伊到付小桐,人类活动造成的大地裂痕(过度开采形成的矿坑在卫星地图上闪耀着危险的白光)与针刺形成的空洞互相映射出关于美与伤害的复杂关系;再从蔡雅玲到Olga de Amaral及赵玉,在对于“金光灿灿之物”的虚幻渴望与诱惑中,在对于某种程度上与女性史同构的殖民史的表现中追问非线性时间中的叙事经纬; 及至姚清妹作品中身体对于“轻/重”二元——在田翊的《赫克力士的房间》(2023)和刘昕的《轨道编织者》(2017)亦有体现——对立律令的拒斥等等,策展人在展览中不断对矛盾之物进行中和与消解。由此,展览便从女性主体的层面上升到对人类存在以及文明普遍境况的关注,在认知到个体差异的同时,以人类个体生命脆弱的普遍性为基础,跨越到与“人”乃至非人生命存在形式直接相关的整体关系建构中。
“燃烧的尺度”展览现场,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2024年。 图片由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提供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垂危现实中,以艺术介入的方式在诸种社会实践中是否拥有某种特殊性?沈奇岚强调,艺术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物质性与直接性。在展览中,女性艺术家的创作依托于各种物质载体,无论是对不同的材料——例如火箭残骸、卫星地图以及文献/档案的运用,还是对技术社会中不同的技术及其理论的讨论与转换,艺术最终以一种感性的、物质性的表征面对观众。通过艺术作品,观众可以身体性地参与到(而不是在抽象理论层面)对于眼下紧迫问题的感知与讨论中,从而“以新的角度和新的尺度重新审视世界的组成逻辑”。
“燃烧的尺度” 策展人:沈奇岚 展期:2024.03.06 - 2024.06.30 上海外滩艺术中心185空间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