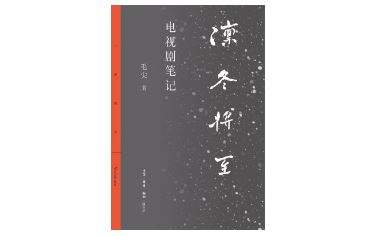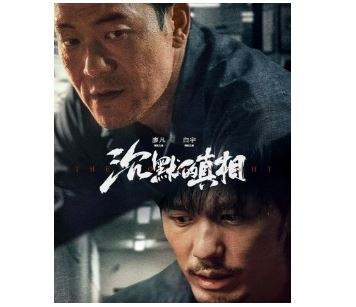|
“刷剧”是很多人的休闲项目。但对作家毛尖来说,“刷剧”还是一种职业道德,甚至带点诙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严肃看剧,专业吐槽,心系国产剧若明若暗、雾里看花的未来。 精力旺盛的时候,毛尖在十家报纸上写专栏。多年下来,市面上的“雷剧”看了个遍。毛尖这么形容她与国产剧的“虐恋”关系:“已经习惯被烂片伤害了,一边被伤害,一边也得到滋养与能量,这种感觉,有点像爱情。” 和很多人一样会,毛尖会“一口气”刷剧,类似知己见面聊个通宵;也会倍速看剧,让烂剧变得可以忍受。 毛尖写的影评,坊间称之为“毛尖体”。“毛尖体”短小精悍,硬朗跳脱,锋芒毕露。对于国产剧,她可谓“爱之深,责之切”。今年6月,毛尖出版新书《凛冬将至》,颇有点国产剧大型排雷指南的意思。 在本期反向流行直播访谈中,主播董牧孜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尖连线。从《隐秘的角落》《摩天大楼》到《沉默的真相》,我们把当下最火的国产剧聊了个遍。“三观”太正的悬疑剧,为什么可能是危险的?国产剧要表达的女性主义,为什么总是发生在女性失恋之后?在冲出国门的道路上,国产剧有哪些爆发潜力?刷弹幕一时爽,烂剧能滋养观众吗?
——下文基于直播访谈内容整理、修订而成,有所增补。 *为了方便大家收听长节目,反向流行已经在书评周刊的微信小程序,以及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蜻蜓FM等多个音频平台上线,在以上平台搜索“反向流行”也可以听啦! 国产剧中的女性主义,往往表现为失恋的应激反应
毛尖:其实我最怕谈女性主义,因为一谈女性主义很容易被各种“吊打”。我们今天不少男女受制于比较浅显、狭隘的女性主义表达,容易情绪化,感情不到位的地方就用女性主义补刀。比如有的女性不想做饭,非拿女性主义来撑场子。用诗人余秀华的话说,“女性主义怎么了?女性主义难道就不能让我为了一个男人而哭泣了吗?”这种观点虽然朴素,倒也有真理性的一面。 国产电视剧中的女性主义词汇和语法,是非常简易的。这种女性主义往往表现为一种失恋的应激反应,这非常荒谬。《三十而已》就很有代表性,三个女主角因为爱情失败,于是分别开始创业、进修和写作,其中一个女主角还成了小说卖出一百多万版权的当红作家。这也太厉害了,这么多年也就只在影视剧里看到。
《凛冬将至》,毛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 《摩天大楼》这部剧整体比较有质感,演员演技也在线,但是这部剧格局还是太小了,基础逻辑太薄弱了。《摩天大楼》着重刻画女性情谊,女主角美宝身处险境,于是她的两位姐妹就靠着奇怪的“女性主义”跟警察撒谎,试图保护她。但问题在于,她们都是有相当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的人,为什么不能给美宝想出一个更有力的解决方案?在此剧的任何一分钟都可以报警,但就没有一个人想到报警。用这种缺乏基础逻辑的方式突出女性情谊,我觉得有点瞎搞。《摩天大楼》里的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空疏且缺乏社会链接的身份,使得每个人都显得过于符号,真空,就像保安的一屋子洋娃娃,为出场而出场。 我们的影视剧非常真空,像玻璃罩一样,别说历史脉络,连家庭脉络都看不清楚。当然,这不只是女性主义的问题,我们的电视剧在整体上出现了问题,女性主义的问题是总体问题的一部分。
刊于《上海电影》杂志1962年第一期的《李双双》剧照。
但是作为悬疑剧,它仍然存在问题,我对结尾暧昧的洗白装置尤其不满意(当然这也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不过整体而言,紫金陈的编剧对悬疑剧来说是一种推进。我觉得“十二集”的拍法很好,毕竟我们已经被长剧“折磨”了那么多年。 从《隐秘的角落》到《沉默的真相》,三观越来越正,但坏人也越来越简单。这种悬疑剧里坏人显得太简单了,取消了一定的复杂性,不够烧脑。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几年前的《无证之罪》更好。
电影《沉默的真相》海报。 董牧孜:三观太正的悬疑剧,会有什么问题?
靠道德感来推动的悬疑剧,是类型剧的失败。我认为悬疑剧要有悬疑的能力,要有类型上的建构。为此我还和朋友有过争吵,我说你要看“道德”就去看《新闻联播》好了。2009年的《潜伏》里也有刻画余则成的信仰,但这种信仰有深厚的时代基础,而且和周边人物存在强有力的对话关系。余则成是信仰,那李涯的行为为什么称不上信仰,还有谢若林的信仰,都对整部剧的信仰问题进行了拷问。 但《沉默的真相》中的道德和信仰,实在单薄,而且每一次道德行动,都被弱智的坏人带了节奏。不过,也有朋友觉得我过于天真,他就用光天化日发生在最高学术机构里的事情教育了我,这样的男主,这样孤独的道德英雄是存在的。 董牧孜:国产剧的叙事瑕疵,似乎也套路化了。包括那些现实主义作品,叙事上也总不够“写实”。 毛尖:国产电视剧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够准确。为什么说不够准确?比如《摩天大楼》里,女主角美宝把恶人养父绑在家里关了一年,但那一年里吃喝拉撒的生活细节全是真空的,按理说,应该留下脏乱差的生物痕迹,但警察来了什么都找不到。几秒钟的时间,这些痕迹全部被清扫了,一根头发一个指纹都没有——而就这,还是整部剧的逻辑起点,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回头看希区柯克的《惊魂记》,打扫尸体整整用了七分钟,但整部电影也就不到两个小时。我能忍受国产剧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但太不准确就是胡编乱造了。所以国产剧道路还很长,如果精确度不够拿道德、情怀来凑,这是很大的问题。
电影《惊魂记》剧照。 人们经常说中国电影工业怎么样,但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电影工业,它还没有建构好,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精确度的问题了。在《和平饭店》里,陈数只提一个小箱子出门,却连续换了二十几套衣服;女主角一早醒来,脸上带妆,眉毛画得比阮玲玉还要精致。虽然很多人骂美国电影(我自己也一直加入这个行列),但美国电影工业的流水线是到位的。有时候想想,电影工业的确是危险的东西,但我们都还没有走到电影工业那一步,关键是技术还没到位。 在国产剧里吃榨菜,才算是本土的文化输出?
不过,起码有三种类型剧是我们国产剧的强项。一种是历史剧,《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悬崖》《黎明之前》《北平无战事》等都很不错。中国革命史的传统是很多国家所没有的,这使得20世纪历史剧成了我们独特的类型,这也是我们可以做大做强的地方;第二是谍战剧,谍战剧和历史剧相互重叠的,也有分野;第三是武侠剧——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是武侠迷。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占据的位置,大厦要立桩才建,这些就像是我们的三个桩。 如果要向前走的话,文化资源,历史传统,都要牢牢抓住。我的理想就是,我们一边能向较高的文化夺权,一边能合乎群众,这是我们能够赢得的文化地盘。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我尤其痛心的是,我们影视剧中对于饮食的表现太差了,美食成了一种表现争吵、打架的工具,我们大概是在荧幕上最浪费粮食的一个国家了。日本电影中极少用掀翻饭菜的情节来表现争执,他们对食物非常珍惜。 文化输出其实是非常润物细无声的。在这方面我们要向韩国学习,你看他们的顶级富豪也好,千金也好,不论是恋爱还是失恋都要依赖韩国炸鸡。在《来自星星的你》里,外星人虽然不吃东西的,但他很喜欢看女朋友吃泡菜、吃炸鸡。 可是,我们国产剧中却很少给中国的榨菜露脸。我们总喜欢去那些有异国情调的地方,恋爱中的男女经常去日本、美国、欧洲。比如几年前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两个人恋爱时跑到帝国大厦去。帝国大厦其实是最不能抒情的地方,这个情节真是活见鬼。相反,《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面条和火晶柿子则是有效的推销,这是一个被我们忽略的文化副产品。 我们的文化输出有时候很奇葩。比如耽美剧里中国大学的条件非常好,处理得粉嘟嘟的。于是就有泰国的耽美粉丝团跑来中国上学,误以为中国大学宿舍都建设得这么好。我们对文化输出有个很大的误会,认为只有表现得强大和发达才叫输出。文化输出其实是整体性的东西,你必须让人感受到你有多喜欢在自己国家的餐桌上吃一碗自家的米饭,那才是文化输出。 董牧孜:说到文化输出,我马上想到了李子柒。她在海外Youtube上很火,从视觉层面展现中国传统之美,细节很考究。你在《凛冬将至》中提到,《风起长林》这样的电视剧体现了中国之美,但不能够准确刻画当下的冲突。你会觉得《风起长林》这样的美学输出是比较单向的吗? 毛尖:这种输出是很有意思的。我的韩国学生跑来跟我说《风起长林》很好看,他不是在说剧情多好,而是说你们的剧组看起来好有钱,比韩国剧组有钱多了。韩国剧组会用纸龙,而你们用的是木头龙,是更高贵的龙。能做到这一点也挺了不起的。这部剧的布景很好,刻画了唐诗宋词般的意境。最近的《清平乐》也在道具、服装和饮食的还原上很下功夫,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刻画的准确性,就不会有那么多网友热衷做电视剧细节的历史考证了。 “烂剧“ 也有自己的时代角色
电视剧《鬓边不是海棠红》剧照。 现在我们影视剧里的双男主角配置太多了,已经变成陈词滥调的营销手段。像《鬓边不是海棠红》《民国奇探》这种剧,因为没法直接表现“基腐”,就塑造成了“社会主义兄弟情”。其实“社会主义兄弟情”是很好的内容,但因为被“基腐”主题抢夺了地盘,也没办法直接表现兄弟情的本色。这种妥协对两种话题都是伤害,于是就陷入了内卷化的循环里。 董牧孜:看国产剧的时候,总少不了吐槽电视剧的时长问题。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后面过于拖沓冗长的剧情,被你称作“影像官僚主义”。批评今天的注水剧时,你也援引艾柯的理论,说“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如果主人公从A地到b地的时间超出你愿意接受的程度,那么你看的就是一部色情片”。不过现在人们看A片似乎也会拉进度条了。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毛尖:烂片基本上是黄片的节奏。有点类似琼瑶剧里“我爱你,你爱不爱我”之类的台词反复说,不断进行语义重复、节奏拖延。武侠剧或悬疑剧如果具有这种烂片的构造,剧中的紧张感就会被消磨掉。 董牧孜:所以,刷剧、倍速播放就成了我们看国产剧的常态。你自己的观看习惯发生了哪些改变?这种改变会塑造什么样的新观众,会如何刺激创作生态? 毛尖:很多人都会“一口气”刷剧,有种“扑上去”的刺激感,就像遇到好朋友一定要聊通宵一样。我们最早都是用电视机看剧,后来觉得不过瘾就看DVD,像《24小时》《潜伏》我都是一口气刷完的。我自己看坏过三四个步步高影碟机。 倍速看剧一方面省了时间,另一方面也让烂剧变得可以忍受。倍速看剧,烂剧也会加一星。当然,好剧是舍不得倍速看的,比如看《权利的游戏》前几季,有种“不虚此生”的观影感受。 烂剧制造了非常多的弹幕观众。年轻一代已经非常习惯开着弹幕看剧了,有时候甚至弹幕都遮住了画面。烂剧造成的弹幕关注,可能为以后的电影形态,准备好了新的观众群体。烂剧也激发了很多创造力,比如有人会把烂剧的素材剪成鬼畜。这就是烂剧带来的时代贡献,烂剧也有自己的时代角色。 被烂片所伤害也被烂片所滋养
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最终季剧照。 毛尖:这些年我一直在写电视剧专栏,作为职业道德,我基本上也要把所有剧集看完才能去写那一千字的小文章。其实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被烂片伤害了,一边被伤害,一边也得到滋养与能量,这种感觉有点像爱情。 不过,现在不是有弹幕了吗?弹幕里有高手。追《权力的游戏》最后一季时烂尾,网上一片鬼哭狼嚎,大家一起弹幕吐槽,找到了共同体的感觉。今天全世界的网剧都是高开低走。美剧剧组花十倍精力去做导航集,但结局就没那么用心了。《权力的游戏》拍到最后,即使是HBO这么伟大的公司也让它烂掉了,就像ICU的病人放弃治疗了一样。国产剧制播方式不一样,全剧谈判,反而导航集和烂尾的现象被平摊了。 董牧孜:你的影评、剧评往往短小精悍,语言风格独特,俏皮、硬朗、跳脱。业界和读者能一眼辨认出 “毛尖体”。贺桂梅在《凛冬将至》的序言里夸你有“与文字浑然一体的写作状态和持久的创作力”。你自己怎么看“毛尖体”? 毛尖:所谓“毛尖体”,是以短平快的方式、以普通读者的视角来写文章。这是长期写专栏的一个结果。其实说白了,我的写作追求是非常电视剧化的,非常人间,往好里说是接地气吧。精力旺盛的时候,我在十家报纸上写专栏,现在就几家,也越来越写不动了,一星期写一两篇。 除了作家,我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学老师,“毛尖体”可能也说明我不太会用非常理论化的方式来写影评、剧评吧。报纸上的专栏都是千字卡死的,用学院派方式来写的话,可能一个要征用的理论都没说清版面就终结了。 董牧孜:在以前的采访中,你提到有朋友本来不打算看剧,看了你的差片影评,觉得吐槽太过精准,于是被“反向安利”。你自己怎么看影评人的角色?会觉得影评人也是“雷剧”大火的助推手吗? 毛尖:雷剧助推手啊,这对影评人而言既是好名声,也是坏名声。当年有个非常烂的烂剧出来,制片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写篇评论。我说太烂了没法写,于是他很兴奋地说,没关系,你骂好了!我一下子觉得作为一个影评人实在好惨,不论我们竖大拇指还是竖中指,对他们来说其实都是流量,可见影评人的地位有多低。 (责任编辑:) |